 34 来源: 索比光伏网 2024-09-13 14:55
34 来源: 索比光伏网 2024-09-13 14:55 “西电东送”,是依据中国能源禀赋制定的重大战略决策。然而,在能源转型的新时代,风光火打捆“西电东送”的模式,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严峻挑战。
近日,国家审计署发布报告,指出风光大基地项目存在资源浪费问题(见华夏能源网&华夏光伏此前深度报道《审计署报告“拷问”风光大基地:个别项目三年累计弃电50亿度!》),称由于大基地开发利用缺乏统筹,很多项目因缺少配套而利用率低下,个别已投产项目2021年以来已累计弃电50.13亿千瓦时。
新能源大基地包括风电、光伏大基地(单体项目100万千瓦起步)和“沙戈荒”大基地(单体项目1000万千瓦起步)两类,新能源装机规划总量超过6亿千瓦,体量接近30个三峡电站。如此规模浩大的新能源建设和远距离输送,是人类能源利用史上所罕见的。
24年前,为了帮助云南、贵州部分地区摆脱贫困,2000年8月初,在北戴河会议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建议,在贵州、云南建设1000万千瓦水电,然后将电送往广东。自此开启了轰轰烈烈的水电、煤电外送工程。
此后二十年间,云南、贵州、四川的水电,以及陕西、山西的煤电,通过“西电东送”通道,源源不断输送至东部经济大省。浙江、山东、江苏、广东等负荷大省,外来电规模甚至占到了用电总量的三四成之多。
“西电东送”在协调东西部经济发展、加强能源电力保供上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如今随着风光大基地强势崛起,“西电东送”的内容在发生变化,新的“西电东送”面临新的挑战。
这既有来自空间地理格局的转换,更有来自风光代替水火的电源特性的骤变。能源大变局下,“西电东送”该如何应对新问题和新挑战?
送端面临“两难”
“西电东送”规划伊始,为实现长距离少损耗送电,电网建设成为首要难题。为了能够远距离低损耗送电,特高压工程得以大规模上马。
然而,随着“西电东送”从传统送端省份四川、云南、贵州、陕西、山西,向风光资源丰厚的青海、宁夏、甘肃、新疆、内蒙古转移,“西电东送”向西部更纵深处转移,这对全国电力流向整体布局提出了更高要求。
由于西北送端基地与中东部地区距离进一步增加,新增直送东部地区电力流向,布局复杂性进一步上升。同时,新能源大基地装机规模巨大,一般在千万千瓦量级,可靠外送需要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技术(7月29日,国内第一条特高压柔性直流——甘浙直流获批,该通道途径6省区,线路全长2370公里,总投资约353亿元)。

甘肃—浙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武威换流站效果图
此外,西北地区的脆弱网架也面临严峻考验。由于大型新能源基地通常位于地理环境异常恶劣的偏远地区,西北电网以750千伏交流为主网架,新疆、青海、宁夏的电力都需要经过甘肃的狭长地带汇集后外送,与东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500千伏环网网架相比,西北网架结构相对薄弱。
而改造和翻新西北网架,无疑需要好大一笔投资。即令是西北网架改造完成了,也存在一个利用率的问题。
特高压送电是有考核指标的,包括整体利用率、输送绿电比例。现实情况是,2023年全国跨省跨区直流输电通道平均利用率约70%,全国跨省跨区输电通道输送新能源电量占比约18%。利用率不够,这意味着动辄耗费二、三百亿元建起来的特高压,存在资源闲置与收回成本难的风险。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之下,国家要求特高压输送绿电比例达到50%,如果“西电东送”的绿电比例始终处于低位,那“双碳”又怎样去实现呢?这本身也有违建设风光大基地和“西电东送”的初衷。
当然,这也不全是电网的问题,风光大基地严重缺少支撑性电源也是原因之一。例如,拥有近2200万千瓦光伏、近1000万千瓦风电的青海,按照设计通过青豫直流向河南年送电400亿度,但是直到2023年全年实际送电量也不及设计能力的四分之一,内中一大原因就是青海缺少与风光配套的支撑性电源。
那为何不抓紧建设煤电等支撑性电源呢?因为在西北省份,光伏、风电是主力电源,建设煤电等支撑性电源则成本过高(煤炭运输成本高昂),并且条件不足(省内用电负荷匮乏,建成煤电后没有用电需求)。
即便配套了煤电,如仅仅是为风光大基地做系统备用,煤电利用率就很低;不配套煤电作为支撑性电源,风光大基地就“转”不起来。这一“两难”课题,短期内恐怕很难有解。
受端有苦难言
由于风光发电与生俱来的随机性、间歇性、波动性特征,外送采取的是“风光火打捆”。但现有的模式下,受端省份也是有苦难言。
目前,跨省跨区送电的基本框架是国家优先计划“托底”、省间中长期交易为压舱石、省间现货交易调余缺。“西电东送”外送电量,绝大部分是经送端与受端政府层面协商从而签订电力交易中长期合同。
所谓电力中长期交易,是指发电企业、电力用户、售电公司等市场主体,通过双边协商、集中交易等市场化方式,开展的多年、年、季、月、周、多日等电力批发交易。现行的交易“说明书”,是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在2020年6月修订后发布的《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
然而,风、光绿电代替水电火电成为“西电东送”的主力电源后,新的问题来了:政府间协议的签订难度陡增。买卖双方博弈的难点是,送电曲线怎么去协调确定。
随着受端各省新能源装机占比不断提升,特别是负荷中心地区分布式光伏装机占比不断提升,从西部大型能源基地送出的电,其出力特性与受端省内新能源出力特性近似,这就导致,外送曲线难以满足受端省份分时段的电力需求。
退一步讲,即便受端省份对风光大基地输送过来的电量“照单全收”,在签订中长期合同时,也必须要考虑送电曲线确定的难题。
水电火电外送时代,由于水电火电是可调节电源,很容易就能与中东部省份的负荷曲线相匹配,签约十分简单;风光外送时代,风光都属于“看天吃饭”的电源,其送电曲线与受端的负荷曲线匹配度非常差,换句话说,受端根本不知道“能够从送端获得多少可靠电量”。
中长期合同之下,当一个受端省份用电需求巨大,就很容易产生电量偏差。要解决“电量临时不够”的问题,就需要通过省间现货市场(与中长期交易相比,现货交易主要开展日前、日内、实时的电能量交易)去找补余缺。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余缺的电量,波动范围往往很大,并且由于现货市场的电价实时波动,需求方要承担价格风险,有时候这对受端省份来说简直就是“不可承受之重”。

三条特高压线路可以向浙江省送电
以外来电高达三成以上的浙江为例,2022年7-8月,持续高温席卷浙江,浙江加大了跨省购电力度。然而,恰是由于中长期市场产生了电量偏差,浙江只好从省间现货市场大举购电,这些外来电的度电电价往往是3元、5元甚至是10元。结果是,仅2022年7月、8月两个月,就造成了浙江省内电力市场总体亏损49.9亿元和38.44亿元。
除了发电曲线和外送电量的艰难博弈之外,政府协议外送价格与受端省内市场化上网电价衔接难度也是非常之大,在前述《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新规中,也并未体现与现货市场如何接轨。
目前,电力现货市场已经在大部分受端省份铺开,形成的分时价格成为送受端价格协商的重要参照,传统外送电“一口价”协议价格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大基地外送价格协商需求。
由于各受端省市场化建设程度不同,价格形成机制存在差异,外送电分时价格协商难度不小。这一烦恼,同时也困扰了西部的新能源大基地——由于中长期电量合约是要刚性执行,外送电的曲线一旦偏离交易计划,基地项目就需要支付额外的偏差成本。
在这种“两头难受”的境况下,很多已投入运转的大基地项目迟迟找不到受端接收方。
以内蒙古区域内“沙戈荒”基地项目为例,四大基地每个项目规划新能源装机1200万千瓦,目前分别规划配套建设蒙西至京津冀、库布齐至上海、乌兰布和至京津冀和至冀鲁豫、腾格里至江西四条特高压。
其中,蒙西至京津冀这条通道,已经纳入“十四五”规划。这条通道计划落地河北省沧州市,但现在,河北省内的分布式光伏特别多,河北南网电力也是过剩的,加之蒙西与河北的新能源出力曲线相近,又增加了外送难度,两省的协调面临很大难度。
一边是送端压力大,一边是受端不积极,“西电东送”早已脱离了传统的水电火电稳定外送的既定模式。“西电东送”这一为电力保供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老革命”,亟需找到顺畅解决新问题的新办法。
免责声明:文章内容仅供参考,本平台对文中观点不持任何态度,文章原创或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发表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站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如内容有不实或者侵权,请马上与本站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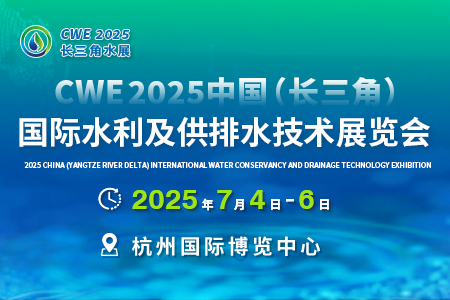












 官方公众号
官方公众号
 微信小程序
微信小程序
